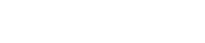【对话】韩嘉玲:农村小规模学校蝶变与探索的中国经验
作者:来源:政策研究中心发布时间:2019-12-23
编者按:农村小规模学校(也叫乡村小规模学校、微型学校、微校或小校等)主要指不足100人的村小学和教学点。截止2017年年底,我国有农村小规模学校10.7万所。乡村小规模学校是我国教育体系的“神经末梢”,在服务农村最困难群体、巩固提高义务教育普及水平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韩嘉玲老师系我院经济与社会研究院讲座教授,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她的研究领域为农村发展、农村教育、人口迁徙、社会发展等。她因在扶贫领域研究及实践中的突出成绩,获得2004年中国消除贫困奖科研奖。近年来,韩嘉玲老师关注中国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发展与变革,其主编的《小而美: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变革故事》于今年付梓,IESR特对韩嘉玲老师进行了专访,整理校对后经韩嘉玲老师同意,发布于此,以飨读者。
一、“农村调查中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您一直以来关注农村问题,最初为什么对农村产生兴趣?
韩:我是一个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典型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对农村世界根本不熟悉。1991年在北大读博时我的研究方向是发展研究,我同级的同学们多半都有上山下乡的农村经验,因此每每在争论有关中国的发展方向问题时,他们最常说的是“你不了解中国农村”。这话就像是个大棒子似的,让我无言以对,也没有再讨论下去的基础。所以我就下决心一定要好好了解中国农村。因缘际会,从1991年开始参加了民间组织“滋根”在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这开启了我认识中国农村的一扇门。博士论文写的就是贫困地区的农村妇女发展,在研究的同时也参与了许多农村扶贫的工作,去了西南、西北的很多农村地区。
时间飞逝,一晃眼就快三十年了,我从当时什么都不懂被戏称“有千万个为什么问题”的年轻人步入老年了,中国农村的发展更是让人惊叹。我第一次踏入的农村是贵州省黔东南的雷山县,这是我博士论文的田野根据地。90年代我从北京要坐两个晚上的火车一共33个小时才能到达黔东南的首府凯里,再搭乘长途车到雷山县城。当时挤得水泄不通的长途车,行李和畜禽等都放在车顶上,摇摇晃晃的近二小时才能到县城,再从县城找拉货的车把我们放到一个连地名都没有,当地人俗称35公里处的地方,然后长途跋涉到当时还未通公路的方祥乡。当地人走的快,大约五六个小时就能到,我足足走了10个小时,一直走到筋疲力尽。每次从北京去调研一趟大约就要花费三四天的时间才能到目的地。不可思议的是,从2015年起,这个“地无三里平、人无三两银”的贵州,已经完成了全省县县通高速的地步。
研究的过程很辛苦吗?
韩:大家都认为我们下乡调研很不容易,其实我自己一直没觉得辛苦,反而乐此不疲,因为每次下乡我都有很多不同的体验与收获。近三十年的农村调研经验,让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原本我们以为理所当然的道理信念、价值与行为,其实不同地域、不同生活条件、不同民族、性别、阶层的人,有着完全不同的认知和价值观。通过田野,我们可以真实地感知不同的人群,他们如何生活,如何在其所处的环境中顺应自然,寻求因地制宜的生存之道,及衍生出的一种生活态度。雷山县是苗族聚居的山区,苗族先祖因生计选择及远离战争而栖居到这片大山里,面对缺乏土地的山区,他们精心地使用着每一寸土地,层层叠叠开垦的梯田就是他们千百年来的智慧与辛勤劳动的结晶。第一次看到这样壮观的景象,我就被这个民族与大自然的对抗所折服。更让我叹为观止的是,水稻田里还养着鲤鱼,这就是所谓的稻田养鱼。稻田养鱼这种古老的共作体系蕴藏着农民的智慧。首先鲤鱼养在稻田里可以吃掉落的稻穗及田里的杂草、叶蝉等害虫,免去了农民拔草的辛劳或使用农药和除草剂,同时鲤鱼在水田里生活,还可以发挥松动泥土、给水稻提供氧气的作用,促进水稻生长。鲤鱼的排泄物成为施加给稻田的有机肥料,这样农民就无需使用化肥种地了。这种相克相生、种养结合的农耕方式,成就了苗族作为“稻饭鱼羹”的民族。用现在时髦的话,这样的农耕方式不就是所谓的生态农业与循环经济吗?
还有几个画面到现在还是活生生的映在我脑海中:就在贵州的梯田,苗族妇女将身后背着的孩子就放在田埂边时,不到两岁的小孩子就在田埂边上摇摇晃晃地玩耍着,我紧张地盯着那个儿童唯恐他掉到水里头,而当地人却司空见惯,觉得我大惊小怪。小孩不放在田埂旁,难道放到家中无人照顾吗?生活的现实使得这群农村儿童就是在田间地头长大的。这些种种的经历都给了我很大的冲击及思考,也是我一直醉心于农村研究的动力。通过田野调查你真的会发现,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设计的问卷其实很荒谬,只有真的到现场当中,才会发现问卷设计背后不知道的故事,这是做田野调查最大的乐趣。因此一直到现在,我还是非常愿意下乡。社会科学的研究,若只是坐在书斋里制作问卷、撰写访谈大纲,而不是从田野中发现问题,那只是完成个人的学术成就而不能对话与直面社会现象。
二、“研究成果要直面社会现象”
您在书里把自己定位为“农村研究发展的行动者”,您如何定义“行动者”?
韩:行动者的意思是,研究的成果不是单纯为了学术上的兴趣或发表,而是强调研究能反映与解决研究对象的问题。比如说本书(《小而美: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变革故事》)就是基于这样的想法而写的。这本书的目标群体主要是面向教育一线的中小学老师、教育工作者们,特别是农村的教师,希望教师们可以互相借鉴其他小规模学校如何因地制宜提升办学质量,突破困境,探索出可复制、低成本的成功经验。在寻找小而美的农村学校过程中,研究团队也参与了小规模学校教师的成长与培养及推动小规模学校联盟的建设与推广。
在本书调研的过程中,有没有令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韩:一开始到一些农村小规模学校调研时发现学生从原来的几百人萎缩到只有几十个人,学校老师担心哪一天学校也会被撤了。老师的精神面貌都不好,就像打败仗的公鸡泄了气似的,他们对学校的未来没有憧憬与希望。他们在远离城市的农村默默的、孤寂的工作着。随着小规模学校联盟的建立,他们才发现有如此多同行,并慢慢认识了许多全国志同道合的学校。在联盟里面,他们通过线上线下的培训与网络交流,分享自己的教学经验,比如某一位老师做了一堂乡土课程,另外一位教师探索了一门综合实践课,他们都纷纷放到群组中“秀”成果,形成一种良好的竞赛和相互学习借鉴的氛围。联盟与区域共同体的成立,说明了农村教师已经不再是散落在偏僻农村的孤独战斗者,他们运用联盟共同体的力量努力克服城乡资源的巨大差异。他们通过相互学习、分享资源、共享经验、共同成长,成功地将散落在大地的珍珠串连成一股农村教育改革的力量。他们孜孜进取,在各地努力实践探索,将为“翻转”中国农村教育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网络课堂给农村教师和学生打开了一扇通往外界的窗户。一方面,教师受到外界新的理念、方法、教学软件等激发,拥有了教学热情,找到了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学生通过直播课程与来自其他地方的学生竞相展示自己的学习能力,形成一种良性互动。这样,课堂不只局限在农村小校自己班级内的同学,而是可以和来自不同地域学校的学生一起比赛朗诵课文,展示作文、美术作品、手工制品及同唱一首歌。每次直播的镜头转到自己的学校时,这些小规模学校的老师与学生都精神饱满地准备着,以最好的面貌来展现农村小校师生的姿态。这样的新教学组织形式给过去死气沉沉的课堂带来了新的气象。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学生不再孤单地学习,而是可以和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儿童同上一堂课。这样的良性互动鼓舞着他们认真学习。师生们通过网络,以最好的面貌来展现农村小校师生的姿态。
看到这样的变化深深地打动着我,因此希望这本书里面的优秀案例可以激励更多的乡村老师,让他们认识到小规模学校也可以做到高质量的教育。同时,这些案例学校都不是靠外部资源与人才支持出来的,绝大多数是依赖自身的力量与努力探索出来的,因此他们的可复制性与推广性很高,我们团队都希望这些案例对其他的乡村学校是有启发意义的,并通过各种平台来促成这样的改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把自己定位成行动者。
您在过去的研究提出的一些政策建议,是如何影响到了政策的改变,影响到了一群人福利的提高?
韩:1999-2000年,我们在北京的城乡结合处的社区进行流动儿童及打工子弟学校的调研,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他们面临的一些困境,譬如说没有学上、学校办学条件简陋、缺乏教师、放学后无人看管等问题。从具体的方面,我们首先组织自己任教学校的大学生到调研的打工子弟学校当志愿者老师,倡导公益组织与基金会对学校办学条件的资助;针对放学后无人看管的现象,2000年9月开始我们就在最早调研的流动人口社区(海淀区的四季青乡柴家坟村)成立了社区学习中心以解决课后无人看管、作业辅导及第二课堂的服务。这种在社区开展对流动儿童群体的服务,今天普遍成为社会组织提供流动儿童的校外活动中的主要模式。从宏观政策上,我们研究发现大量的流动儿童面临无学可上的难题;此外,流动儿童的家长需要花费缴纳比城市儿童更多的费用,但却接受质量参差不齐的教育。因此在2001发表的研究报告中的政策建议中我们提出应该让更多流动儿童可以在流入地进入公立学校就读。这份研究报告被北京新华社的记者看到,并让我亲自带他们实际考察了北京的流动儿童学校状况。最后通过新华社的内参渠道,获得当时分管教育的副总理李岚清的批示。其后,我更进一步参与到相关政策的调研中,对促进制定关注流动儿童入学的相关政策起到了一定倡导的作用。这是作为一个研究者最为欣慰的结果。

图为韩嘉玲在暨南大学参加学术研讨会
三、“小规模学校的存在价值不可忽视”
您的新书《小而美: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变革故事》是讲农村小规模学校,是涉及到了农村的教育以及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小规模学校一直都是教育发展问题的末端,很少有人注意到他们,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他们的?
韩:因为我一直关注农村教育及教育公平领域的研究,这也是我现在参与的团队——21世纪教育研究院,长期致力的领域之一。本世纪以来,在教育城镇化及撤点并校等大环境下,我国农村教育的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70年代的“学校办到家门口”、“村村有小学”的格局发展到当前“城挤、乡宿、村弱”的现状,换言之就是县城里面的大班额学校、乡镇寄宿制学校及村里的小规模学校(包括村小及教学点)的并存状况。这些目前仍然留在村里小规模学校就读的学生,多半是走不了、无法走或出去后被淘汰回来的生源,同时他们多半来自建档立卡的贫困家庭。无论从扶贫的角度来说,这些农村小规模学校都发挥了一定的兜底作用,保住了贫困及困境儿童就学的基本权益。从教育公平的视角,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等待着这类学校的自生自灭,让农村的学生无法就近入学,无法获得有质量的教育。现在主流的观点认为办好寄宿制学校就能解决农村儿童的上学问题,从经济效益的角度觉得没有必要保存这类学生人数非常少的学校。我们认为办好农村小规模学校不仅仅是涉及到教育公平以及阻断贫富差异的代际传递问题。从效率的角度来主张或认为用砸钱盖出高大上所盛行的
校舍的办学方式就能办好教育的看法,都是忽略从农村发展、乡村文化继承、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等观点来看待农村教育的作用。
虽然教育部在布局调整的意见中提出:小学阶段以走读为主,农村小学1至3年级学生原则上不寄宿,就近走读上学;小学高年级学生确有需要的可以寄宿。但是我们在调研中却发现仍然有不少三年级以下的儿童寄宿,甚至连幼儿园的孩子都有寄宿的情况。当前普遍的观点认为解决农村学校就是办好寄宿的问题,但是农村学校不是盖好漂亮的校舍就可以解决的,我认为还是要回到办好可以就近入学的村小(多半是小规模学校)。因为在小学的这个阶段,家庭教育与父母的在场还是对儿童成长非常的关键,这绝不是学校教育与老师可以代替的。因此唯有村小/小规模学校的存在可以让农村儿童就近入学,这种入学的可及性是教育公平中最基本的教育机会平等的前提条件。
此外,村小对于乡村文化的传播与继承发挥着灯塔的作用,对乡村文化的振兴至关重要。我们90年代在农村做调查的时候发现,在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大潮下,大量的年轻农村人口外出打工,因此当地人常常形容农村只留下“38,61,99”部队,就是妇女、儿童和老人。然而,随着大量的农村学校的关闭,儿童进城念书,母亲进城陪读,农村中的儿童和妇女也离开农村了,这也是当前农村老龄化的背景之一,也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的空洞化。我们很难想象当农村中没有学校,不再升起国旗,不再有朗朗书声。没有儿童及妇女的村寨,乡村振兴从何振兴?乡土文化如何继承?所以无论是从教育公平的角度还是从扶贫的角度,或是从乡村文化振兴的角度,我们都认为办好村小/农村小规模学校的任务非常重要。
您这本书里面讲了十所学校的案例,他们的培养模式可以说是回归了这种教育的本质,但这并不是主流,那么小规模学校如何推广?
韩:这十所学校是案例研究,是一种典型研究方法,通过解剖麻雀的方式,深入挖掘、展现这些小规模学校面对困境如何探索的具体做法。通过十个学校的不同探索,也可以说从不同的维度来展现农村小规模学校如何变劣势为优势。一方面小规模学校学生少、资源少,又地处边缘,因为没有人关注,对成绩追求的压力小,反而给了他们探索的空间。同时农村小规模学校坐落在远离城市的农村,与大自然有着天然连接,地处偏乡也保留着各具特色的地方乡土文化与知识。这使得学校可以将村庄中触手可得源源不绝的资源转化成教育资源,提供发展学生智慧的火花。很多学校开始跃跃一试,并因地制宜地发展出有自己特色的乡土课程,走出了不同的路径。
农村小规模学校当然不是主流,也无法成为主流,我们只想走一条适合农村学校及儿童的教育路径。长期以来,我国的农村学校的城市化倾向,使得他们面临与城市学校在同一轨道赛跑的窘境。同时,追求成绩的应试教育已经走入了死胡同模式,更多的对教育有热情的人已经在探索新教育的可能,农村小规模学校的种种探索也是希望为“翻转”农村教育走出一条发展新路。
让我们更可喜的是,这些案例也让来自大城市的教师在阅读后得到了启发与感动,让我们相信教育创新也可以发端于偏远地区,农村学校的经验一样可以分享给城市的教师。
四、“如何把流动儿童变成人才留在城市?”
您觉得未来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趋势是什么?
韩:目前我正主编另外一本有关流动儿童的书,在书中研究团队积极倡导:在义务教育阶段各级政府应打破现行以户口为依据的户籍管理体制,建立以常住人口/现居住人口的户籍制度为依据的入学体制。各级政府不仅应为户籍人口服务,也应将非户籍人口(流动人口)纳入其日常管理与服务范围之内。虽然最近大城市所盛行针对非户籍儿童采取的积分制入学看起来,是一种比较科学的衡量标准,可却是一个被人诟病的“拼爹拼妈”入学政策。在积分制入学的要求下,最底层的农民工子女完全被淘汰了。中国很多的问题是很复杂的,比如人口的压力与流动儿童上学的权益,与社会公平之间如何平衡?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把农村学校办得好,做好乡村振兴,是否就没有那么多人到城市工作,这个问题是否就不会这么尖锐?这个暑假我参与我们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学院(IESR)的广东千村调查,在广东省的农村中,外出打工依然在家庭收入里占很高的比重,如果农业收入还是不能足以维持家庭生计的话,那么人口外出依然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还会继续存在。同时因为流动人口中的留守儿童存量很大,根据全国妇联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的《2015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报告,2015年我国留守儿童有6877万,流动儿童有3426万,这6877万的留守儿童随时可能变成流动儿童。儿童与父母一起共同生活、家庭团聚在国际移民里是第一优先被考虑的重要因素。无论是从人道的考虑或者是从子女发展的角度,儿童跟父母一起生活是儿童的基本权利。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问题未来依旧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挑战。
我觉得流动人口子女教育要从更高的视野去看,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 不仅给城市培养了更具活力的新兴力量与未来城市的建设者, 同时也为全国输送了一批有现代化视野的人才。对流动儿童教育的辐射与影响, 无论从提高全民族的素质或从城市对农村帮扶来看, 城市都应该发挥及承担更多的支援全国流动儿童教育的责任。这也是现在实施人才规划战略需要关注的问题,我们不是只关注所谓的高精人才的引进,同时更要培养这些从小就生活在城市的流动儿童,而不是因为现在城市人口太多,就通过各种高门槛的入学要求将他们推回老家去。所以我也很高兴IESR的老师们很关注这些议题,冯帅章院长从上海到广州一直都关注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并致力于推进政策解决。从理念上我和IESR还是比较有契合点的,流动人口各类问题在特大城市的解决还有待努力,所以在这些方面的研究与倡导上我们还要继续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