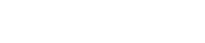乡村里的“留守二代”:谁能改变他们的命运?
作者:来源: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发布时间:2018-12-18
10月29日,由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发起的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调查正式拉开了2018年第二轮基线调查。该项调查由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教授James J. Heckman担任项目顾问,中美两国研究团队共同对项目研究课题及问卷内容进行支持。在今年的调查中,财经记者跟随调查团队进行跟访,写下了这篇报道,我院进行转载,以飨读者。
在中西部农村,学龄前留守儿童增多,留守年龄越来越小,单亲留守更加普遍,“留守二代”成长环境更令人担忧
《财经》记者 熊平平 | 文 朱弢 | 编辑
在城镇化大潮下,上世纪90年代开始,农民大规模离开农村到城市务工, 但因为城市的学位资源门槛高筑、高考制度及一系列户籍限制,这些农民的子女只能留在农村成为留守儿童。
30年来,城市繁荣,留守儿童却成为被时代抛下的群体,他们长时间缺少父母的陪护,成长于闭塞的乡村环境,大部分人只能重复他们父辈的命运,继续进城成为农民工。
上世纪90年代的“留守一代”今天已长大成人,并成为了“农民工二代”,而他们的子女却仍然继续在农村留守,成为“留守二代”。
近年来,关注留守儿童问题的呼声不断,相关的政策文件不断出台,但据《财经》记者调查,学龄前留守儿童增多,留守年龄越来越小,单亲留守更加普遍,乡村结构基本瓦解,“留守二代”成长环境更令人担忧。
记者在四川绵竹的调查显示,面对现实问题,基层教育主管单位和乡村学校一直在努力摸索解决方式,绵竹乡村学校通过调动校内资源,补位留守儿童在家庭层面的缺失,一定程度上给留守儿童创造了相对友好环境,但治本之策仍需打破户籍壁垒,有序开放城市教育资源,以吸纳农民工随迁子女。
留守的代价
钟雨桐、黄妤晗是四川绵竹当地的留守儿童,他们拥有相似的童年。
7岁的黄妤晗,在绵竹市新市学校二年级四班就读。“一出生她爸妈就把她留在家中,一直跟着我们生活”。黄妤晗的奶奶说,“她爸爸去了菲律宾打工,很久都没有回家了。”
见到黄妤晗时,给人的感觉就是孤独,略显黑黝的脸庞难见笑容,但眼神清澈,透着聪明。她每天早上6点起床,7点前到校车停靠点,坐40分钟校车,8点前要到学校上课。下午放学后,回到家先写作业,剩余时间就是一个人看电视,基本不出家门。
爷爷奶奶年事已高,两位老人坦陈,除了照顾黄妤晗衣食起居,在学习上没有能力辅导,情感上也难有亲密的沟通。由于父亲远在菲律宾,黄妤晗已经记不清上次和父亲通电话的具体时间。
周末和假期黄妤晗都是一个人度过,大部分时间看电视,稍微幸运的是,隔壁邻居家有位读四年级的姐姐,黄妤晗遇到不会做的习题就去找她请教。
与黄妤晗同校的钟雨桐也是一位“资深”留守儿童,15岁的她已经留守9年,“她小学一年级就由我们带了”,钟雨桐的外公说。
钟雨桐的外公外婆并不识字,在学业上全靠她自学,在钟雨桐房间书架上,十多本二十四史全集整齐排在一起,多本都已被翻旧。钟雨桐说,这套书是妈妈买给自己的,这些年的闲暇时间都是翻这套书度过的。
尽管好学,但钟雨桐的成绩仍然只能排在中游,明年中考,她希望能考上绵竹市南轩中学。钟雨桐说,初二时有段时间找不到方向,又无人诉说,“那时特别迷茫,成绩也下滑了很多”。
钟雨桐似乎比黄妤晗幸运很多,父母半年可以回家一次,每周也可以通一次电话。而黄妤晗则还有希望脱离留守儿童的身份,她偷偷告诉记者,爸爸曾经在电话里答应她明年回家回绵竹工作,“邻居叔叔说可以帮我爸爸介绍工作”。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绵竹当地农民开始往成都、长三角、珠三角流动,而他们的孩子只能留守农村。30年过去后,当年的留守儿童已经长大,而他们的孩子大部分仍无法改变继续在农村留守的命运。当地一项调查显示,绵竹2017年留守儿童占比达51.54%。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社会调查中心针对留守儿童的长期跟踪调查显示,在认知能力测验中,即智商能力测试中,双亲都外出的留守儿童的认知能力最差,一方外出的留守儿童其次,非留守儿童最高;在非认知能力测验中,即情商能力测试中,差异更加明显,父母都没有外出务工的受访学生开放性、责任心和人情世故等维度上得分都更高,而低分则更多聚集在留守儿童群体。
单亲留守儿童越来越多
黄妤晗和钟雨桐都是由祖辈养育长大,性格相似,看上去都非常安静,性格内向,不善于表达,小小年纪却很少露出笑容。
新市学校学生处副主任杨生敏表示,“首先,留守儿童不是问题孩子,但由于缺少父母陪伴,他们的突出问题出现在人际交往和自信心方面”,而这两大问题会伴随多数留守儿童终生,还会影响到日常的生活和学习。
杨生敏的另一身份是新市学校的专职心理咨询师,曾两次参与过绵竹市教育局对全市留守儿童的心理调查。在最近的一次调查中,由于留守导致的儿童心理问题已经越来越引发她的担忧,“很多留守儿童在亲密关系的建立上存在问题,在一次调查中,一位小学五年级的留守女孩告诉我,在妈妈过年回家时,她会对妈妈的拥抱有抵触”,杨生敏告诉《财经》记者,“等他们长大后,会在谈恋爱找对象中出现很多问题,很难建立好的亲密关系。”
还有个别留守儿童存在更极端的心理问题,在杨生敏的调查中,有多位留守儿童对她吐露曾经有过的自杀想法。“一位六年级的女生,成绩很好,在学校看不出问题,但在访谈中我发现她的手腕有割伤的痕迹,后来她告诉我了,父母离异,属于单亲留守,每当深夜想到自己的境遇就会绝望,想通过自杀解脱。”
单亲留守儿童在中西部农村越来越多,多位乡村教师提起这一趋势,杨生敏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留守儿童一代现已长大成人,由于本地适婚对象越来越少,多在外地打工时边工作边找对象,受社会环境影响,两人没相处多久会很快结婚、生子,甚至很多是未婚先孕,但生下孩子后,或因为贫困、或因为两人相处问题,婚姻破裂。
“母亲离开了,父亲必须出去打工,孩子一出生就留给了爷爷奶奶,这些单亲留守儿童已经越来越多,他们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杨生敏对《财经》记者表示。
在校园里,单亲留守儿童问题已经开始部分显现,绵竹市清道小学校长吴华富告诉《财经》记者,“由于溺爱和缺乏管教,这些孩子很难养成好的学习、生活习惯,这些不仅影响他们的学习成绩,还将深远地影响他们的将来。”
与单亲留守儿童日趋增多的同时,乡村也正在以更快速度瓦解。在传统乡村中,不同年龄结构、文化层次、职业身份的村民建构起礼俗社会,一代代人成长其中,既学习社会知识,也不断约束自我行为,与乡村学校共同构建起孩子的完整学习体系。
钟雨桐、黄妤晗两人已经难以在村子里获得学习氛围,村里除了为数不多的老人外,再无其他人群,两人放学后就只能宅在自己家里活动,村民之间的互动极少,她们也难以参与其中学习。
曾有多位学者对《财经》记者表示,正是乡村作为教化功能场所的瓦解,使得今天留守儿童的处境越来越糟糕,他们唯一的学习场所只剩下乡村学校了,但乡村那种非正式的教化是学校的正式课堂无法替代的
学校努力补位
留守儿童已经受到全社会的关注,从中央到地方也都出台了种种关爱政策,但多位乡村学校的老师表示,这些政策大多“雷声大,雨点小”,难有根本性解决方法。
令人稍感安慰的是,乡村基层学校通过种种努力,试图补上父母关爱、乡村教化缺位后留下的空当,它们通过调动校内存量资源,为留守儿童的心理关爱、学习能力、人际交往提供友好环境。
吴华富告诉记者,清道学校的数名专职心理咨询师成为了对留守儿童的心理辅导的重要力量。据绵竹市教育局工作人员曹霞介绍,绵竹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重灾区,当地所有学校都配有心理咨询师,同时也都是在职教师,开始是针对震后学生心理开展辅导工作,但后来他们的工作逐渐扩展到留守儿童,定期对留守儿童展开素质拓展,让他们在集体活动中获得自信。
此外,杨生敏所在的新市学校会针对留守儿童开展诸多“一对一、一对多”的陪护,让年轻老师与留守儿童形成朋友关系,在周末、暑假这些留守儿童最需要陪护的时候组织集体活动。“暑假期间,我们针对留守儿童组织过一场夏令营,两天一夜,我确实看到了很多留守孩子在活动中逐渐变主动。”杨生敏说。
留守女孩在性健康方面的教育一直是乡村最缺乏的,“母亲不在身边,她们都没人指导”,杨生敏对记者表示,“学校这时候就要去引导,由女老师对留守女孩进行培训。”
在对绵竹市乡村学校采访时,记者发现,每所学校都有一个“乡村少年宫”,其中清道学校的乡村少年宫已成为当地典型,学校利用老师和校外志愿者资源,对在校乡村学生进行手工、剪纸、绘画、英语口语等方面的免费培训,留守儿童暑假期间可在乡村少年宫度过。
与绵竹市一县相隔的绵阳市安州区迎新乡小学则通过体育给予留守儿童更多可能性。
11月27日下午4点,迎新乡小学全校300多名学生在操场练习足球,副校长马顺洗担任教练。“我们代表中国去了俄罗斯世界杯参加了开幕式”,练球期间,一位六年级学生对记者说,口气颇为骄傲。

(四川绵阳市迎新乡小学,一支由学生组成的足球队多次在市级比赛中获得冠军。摄影/本刊记者 熊平平)
迎新乡小学留守儿童足球队拿了全市冠军,在当地已成为了佳话。据马顺洗介绍,迎新乡小学留守儿童比例高达70%以上。因缺少父母的教育,很多留守儿童行为习惯差、难于管教一直困扰老师。2013年,马顺洗开始在高年级选拔球员组建足球队,“我把这群孩子组织起来训练,总比他们在家看电视玩手机游戏强吧”。
马顺洗说,经过组织训练,这些孩子发生了很大变化,身体健壮了,性格也大方了,“很多孩子还懂得尊重别人了,不再像以前那么自私。”
学校补位是对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一种摸索,但显然不是治本之策。
绵竹市绵远学校校长张杰先表示,在当前留守儿童问题上,乡村学校固然是重要力量,但是社会不能把所有责任放在乡村学校身上,如果全社会这样呼吁,留守儿童的家长更不会回到孩子身边,认为交给学校就足够了。
“家庭的责任始终是不可缺失的,有条件的家长应该回来陪护孩子,把孩子完全交给学校是错误的教育观念。”张杰先告诉记者,而学术研究也早已证明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James Heckman的研究结果显示,对处境不利的孩子来说,早期家庭教育的缺失比物质财富的匮乏影响更大,家长应该权衡利弊再决定是否让孩子留守。
并非所有的农村家长都愿意承受与子女分离的代价,绵竹市绵远小学六年级的胡宸滔一家就曾试图改变孩子的留守状态,但最终以失败告终。
13岁的胡宸滔一出生就被父亲留给爷爷奶奶,父亲在浙江做司机。他在家留守至四年级时,奶奶心脏不好,爷爷有糖尿病,父亲便把胡宸滔带到浙江,由于父亲没有缴纳社保,无法就读于当地公办学校,胡宸滔只能去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由于教材不同,父亲害怕耽误他的学习,便重新读了四年级。
胡宸滔本以为可以结束他的留守童年,入学半学期后,他就读的这所学校突然告诉他不能继续读书了。就这样,胡宸滔在父亲出租屋里待了数个月,春节时就随父亲回绵竹了。
无奈的胡宸滔再次成为留守儿童。《财经》记者在家里见到他,沉默少言,但私下里他对记者说,自己很珍惜当前的读书机会。胡宸滔的班主任黄静说,读五年级后,他学习很刻苦,和原来顽皮贪玩相比完全变了样,现在成绩保持在前五名。
“看到了父亲在外打工的艰苦条件,我好好读书就是希望明年能考一所好一点中学。”胡宸滔说。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表示,绵竹地区的留守儿童现状并非个案,它一定程度上是整个当前中国中西部人口输出地的缩影,父母为了家庭经济收入,需要外出务工,但他们并不是不想带着孩子去工作城市上学,主要是就业城市对务工人员子女制定的入学门槛太高。
冯帅章说:“目前的户籍制度造成的政策壁垒限制了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获取城市教育资源的机会,有序开放城市学校资源以吸纳随迁子女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治本之举。”
(本文首刊于2018年12月10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记者手记
静悄悄的乡村,孤独的留守
《财经》记者 熊平平 | 文 朱弢 | 编辑
当大巴在成都平原上飞驰时,恰逢大雾,车窗外灰茫茫一片,分不清雾还是霾,沿途树木与建筑若隐若现,这令我想到了即将采访的留守儿童,他们的成长像在这大雾天行走,看不清前方,还时常迷路。
全国到底有多少留守儿童?由于统计标准不同,并不统一,但毫无疑问数量庞大。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7年的数据,中国有四分之一儿童处于留守状态;全国妇联2013年发布报告称,全国共有6102万农村留守儿童;民政部最新的数据是全国有697万留守儿童了。
这次采访是随同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IESR)团队,他们多年跟踪调研绵竹留守儿童,我作为媒体方参与,采访当地老师和学生。IESR是做学术研究,对当地学生和家长、监护人进行问卷调查,而我的采访是记录,走进留守儿童家庭,与乡村老师交流,供读者或多或少多了解一点祖国西南县城的留守儿童的真实状态。
我特别重视此次采访,提前一个月找资料,只为了身处绵竹采访时能够更加从容。因为我也曾是一名留守儿童,2岁留守奶奶家,10岁至16岁留守多个亲戚家,过往经历化成记忆,烙印在脑海,还经常被唤醒。
如果论年龄,我与最小的采访对象相差22岁,两代人,我是留守一代,他们就是留守二代,因为相似的童年留守,采访他们分外亲切。
走进他们的生活时,我会下意识对比我的成长环境,本以为他们的环境已经大有改善,不会再如我当年留守时般贫瘠,但随着调查的深入,我发现留守二代的情况并没有实质上的改善,甚至某些方面更不如意,如家庭的破裂、农村结构的瓦解、阶层晋升的受阻,这些问题比我二十年前留守时更显著。
教化
诚然,留守儿童已是老问题,农村空了也是持续存在的现象,但在讨论留守儿童问题时,把二者结合起来深度观察则不多。
在我留守的童年时段,是上世纪90年代末,农村仍然有大量的老中青在,年龄结构有梯度,不像现在村里只剩老人与小孩。
记得每天放学,一走进村口,就能听到村里大树底下、水井旁边村民的讨论声,年纪大的爷爷、中年的伯伯、青年的叔叔聚在一起闲聊,有时还会有读高中的大学生参与,或聊水稻投入和收成,或聊60年代大集体往事,或者隔壁村选举八卦,抑或三国水浒抗日英雄,所聊话题无所不包,而我们小学生经常旁听,或询问两句听大人解释,因为回家还要被要求写作业,这在村口的闲听显得无比快乐。
近来我常回忆这些旁听村口大人胡侃闲聊往事,他们所聊内容早已不记得了,当年的老人也大多早已去世,但这却是我成长之路上的宝贵资源:村民的聊天,于我们小学生而言,是一堂堂生动的历史、政治、经济、地理课,这些要等到大学才能系统学习的课程,当时的农村小孩早已经耳濡目染。
比如,村里老爷爷会讲三十年代往事,当时日本军队进村,抢了隔壁村大户人家的粮食,毁了宅子,后来我知道了我们家乡曾是多方军队的必争之地,后来共产党的军队就是在这里建立了根据地,慢慢控制了华中地区,最后一步步取得了胜利。
他们还会讲农业生产,讲农历节令与种植时机,惊蛰、清明、谷雨对应着不同的劳作,村民们一代代依历法而活,还会讲一亩亩地收成多少,穿插1968年大跃进“亩产三万九千斤”的“光荣”历史,当我们追问为什么现在收成这么低时,老人们说那时把整个公社其他田里的稻谷割在一亩田里,骗了所有来调研的专家和官员,说完后都朝着我们小孩神秘笑笑,说你们以后就懂了。
甚至“战争”这样的遥不可及的大事件,村民都会绘声绘色给我们讲:隔壁镇里,因为村子与村子之间有土地矛盾,两村村民互相攻打对方,而且都有严密的军事攻防。当时我们最羡慕的就是那两个村里的孩子,可以近距离观看战争。
所有这些聊天,对于小孩来说都是新鲜的,村民们许多细节的铺垫,加上儿时发达的想象力,这些村口的信息构成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而这些就是大学里历史、政治、经济和地理课程要交给学生的,而那些村民利用沼气做能源更是生动的化学课程,利用杠杆运输石头则是物理课。
等等,等等,不同年龄段村民的人生经验都汇集在村口,每天等待小学生们的旁听。
我现在想来,这就是乡村的教化功能,在相对完整的村庄结构里面,晚辈会通过长辈积攒的人生经验来完成各种知识储备,也在与大人的互动中学会基本礼仪与规矩,也正是这种教化功能弥补了乡村小学教育的诸多落后,稍有天分的孩子能够在村小教育与乡村教化中间吸收营养,后天勤奋刻苦者都能走出村庄,改变自己的命运。
但现在的村子,一走进村口,你就会发现极其安静,除了几声狗吠声外,再无闲聊的村民们,村子只是小孩子回家的一条路,路上不再有长辈们的“村庄课堂”,也不会有乡村礼仪的训练,我自己老家的村子是这样,绵竹农村也是如此。
瓦解
传统村庄对于小孩子的教化已经基本瓦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作为记者,我是在不断的阅读和采访中,其中原因逐渐知道一二。
从我记事以来,这种村庄的瓦解并非一夜之间。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农村生产力不断得到解放,粮食开始富裕了,很多农民不再守着一亩三分地耕作,开始离开土地去城里打工。在我记忆中,1995年前,我们老家村民有两种选择,去附近乡镇县城的企业工作,或者去沿海城市谋生计。
我父亲早年就是去了县城的企业做事,做木材生意,买树卖树,为当地县城的发展建设提供原材料。印象中他会经常回家,带着从县城买回的苹果、橘子更是我童年最大的期待,如今我的记忆中总能浮现那种甜酸味,或闻到这种味道就能唤起往事。除了父亲经常回家,我和母亲也经常会去县城找父亲,在他的出租屋里一起吃饭 。
但1995年以后,政策变化很多,对农村土地上的非农建设项目逐渐收紧,1998年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进入非农集体建设使用的口子更是大大缩紧,“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几乎直接堵死了乡镇工业化的通道,中西部发展空间也在这一时间被挤压,所有的资源要素都流入东部沿海和省会大城市。
在这种背景下,农民离开土地后则被推向了大城市和沿海地区,我父母也是在这种洪流下,离家千里之外,去了苏州,在当地进了工厂,成为农民工,而我留在了村里,与父母相隔万里,跟着亲戚生活,开启了我的留守生涯。
二十一世纪开始,农民进城规模更大,村里但凡有点头脑和追求的农民都要出去打工,留在村里会被乡民们瞧不起,年轻一代大多初中一毕业也都跑进了沿海工厂,像我这样继续读高中的是少数,而村里只剩下老人、妇女和小孩,当时村民们被称为“993861”部队,村庄原来的组成机构基本瓦解。
村庄不再热闹,狗吠声已经是今天留守儿童对村庄最深最鲜活的记忆。这几乎是全国99%农村的现状,99.9%的乡村留守儿童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
孤独
村庄静悄悄,这是我这次采访最真实的感受,而这些乡村留守儿童真的很孤独。
这次在四川我采访了多位留守儿童,一出生就由爷爷奶奶带着,见到这些孩子,从他们的脸上总能读出孤独感,那是太久都没有感受到爱的暗淡,是太久缺乏信息交流的隔阂,不是城里孩子那种活泼、充盈与茂盛,是会把自己埋藏起来的张望与沉默。
孤独,这是我见到这些留守儿童后脑海里一直冒出的一个词,此前我对孤独这个词仅仅停留在动物身上——大海的海龟,它们数百年都是独自活动,在茫茫大海中游动,但这一次我可以将这个词投射到具体的人身上,一种巨大的冲击一直萦绕着我。
这种冲击,不是同情他们,而是我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于我,留守至高二时,我父母选择回家,我也就结束了留守,后来上了考上了大学、工作,对于留守儿童的认知一直停留在我自己的经历,而且这些年多生活在城市,见了太多城市里丰盈的孩子,以为所有孩子大多都这样,而过年回老家时,村里的留守儿童父母也回来了,在父母身边他们多半是开心的活泼的,让我忽略了这些差异。
我采访过的每一个村庄,都是静悄悄的,不再有往日数个老农围坐一起的闲聊场景,孩子走过,听到的都是自己的脚步声。而村庄里的爷爷奶奶,也因为村庄少了儿女的陪伴,心情郁郁,哪里来的心思去村口闲聊。
我采访了一个四川小女孩,7岁,黑黝黝、胆怯怯,但她的眼睛很是清澈、聪慧。爸爸常年在各个城市工作,最近去菲律宾打工了,从小陪着爷爷奶奶生活,她的成长像极了一部默剧,每天都和自己玩耍,唯一的玩伴是邻居家姐姐。采访结束时,我给她拍照,她站在院子门前,表情孤独,我让她对着镜头笑一笑,她一直拒绝。
临走时,她告诉我自己的新年愿望,她希望爸爸早点回来工作,她还说爸爸还答应她明年就回来。
我希望她的新年愿望能实现,爸爸明年就回来陪伴她成长,让她结束留守的童年。我也希望,这些留守儿童的成长不要再如“在严重雾霾天行走”,让他们和城里孩子一样开心、健康,也不要再让他们的孩子成为“留守三代”。